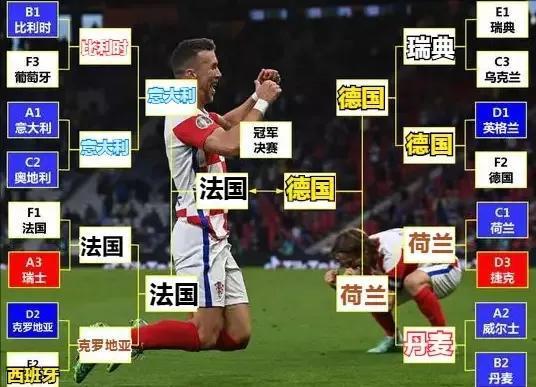◎罗皓菱窦文涛
6月20日,《圆桌派》第七季如约而至。
当一篇题为《当窦文涛已成往事》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疯转之际,此刻《圆桌派》的归来让不少老观众奔走相告,“人还在呢!”
这一季的第一集中,窦文涛、许子东、马家辉、陈鲁豫老友相逢,不禁让人想到美剧《老友记》。与剧中那些陪伴观众一起成长的人物一样,“窦文涛和他的朋友们”也陪伴我们度过了漫长的时间,从上个世纪末来到此刻的2024年。只是,他们手上没有剧本,台词也都是即兴的,素材来自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。
作为这出戏的灵魂人物,窦文涛既是导演,又是演员。大概由于一直条件有限,场景往往只有一个,一张桌子,几把椅子,演员也都是亲朋好友。
从电视时代进入互联网时代,语言类网综《奇葩说》《脱口秀大会》等节目相继火爆荧屏,“观点”和“情怀”成为流量密码。而在这张圆桌上,窦文涛说,相对于“观点”,他也在乎“语言”;相对于“情怀”,他觉得更好玩的是“人的状态”。
“看法总会过时……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。”作家余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,这其中涉及艺术的伦理。在某种意义上,与其说窦文涛是一名谈话节目主持人,不如说,他在骨子里,是一位“聊天”艺术家。
会不会听聊天是更重要的一件事
北青艺评:《圆桌派》来到了第七季,有没有感觉到七年之痒?
窦文涛:《圆桌派》的历史其实有八年了,时间长了反而生出一点使命感。我这辈子就靠聊天吃饭了,本是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,突然有了点使命感。如果说“脱口秀”推广了“单口喜剧文化”,“奇葩说”彰显了一种“辩论文化”,我想我也推广一个什么文化,那我能推广的就是“聊天文化”。今天看着互联网上种种的恶,我有时候就会有一种还能不能好好聊天的感觉。当下人与人之间的很多问题,是因为大家不爱聊天,不爱面对面地聊天,也不会聊天,也就越来越不会聊天了。
北青艺评:人和人之间面对面带有体温的交流是道德的基础,这是哲学家阿甘本“邻人的哲学”涉及的一个观点。包括项飚老师讲“消失的附近”其实都在讲远程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,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困难:一方面是网络上话语的泛滥和互相攻击,另一方面是一个具体的人和另一个具体的人面对面交流的困难。
窦文涛:聊天的价值观是什么?起码我聊天的一种价值观是:观点不同没有我们的友好重要。我们连抬杠都是笑着抬杠的,是为了开心。人们为什么聊天?不一定是为了得出个什么结论,还有更多是交流信息、联络感情,或者仅仅是消磨时间。聊天是人类最悠久最普遍最广泛的语言生活、娱乐生活、精神生活。
北青艺评:在你的节目中没有遇到过嘉宾因为观点不同吵起来的情况吗?
窦文涛:这种情况出现得非常少,因为我根本不往那里引导。很多人觉得打起来刺激,有收视率,但是我不喜欢这样,这有悖于我的性格。我觉得我们有别的办法开心,我们用不着看两个人打架开心。

北青艺评:如果你意识到有人说错了,也并没有欲望去纠正他?
窦文涛:这种欲望很淡,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审美观。你要纠正,说明你有一种“对错”的审美观,你认为他说的不对,不对就是丑的,所以要纠正。可是如果观察人表达是一种审美观呢?我喜欢看不同人讲话的状态,非常有意思。说真话有说真话的可爱,说假话有说假话的可爱,吹牛有吹牛的可爱,很好玩。我们心里知道对错就可以了,即便是错了但是他表达很有趣也很好。
会不会聊天是一回事,会不会听聊天是更重要的一件事。我举一个例子,阿城老师讲话很精彩,但是有的学者会说,他讲得不对。他对不对,跟我没关系,或者说他对不对我可以自己回去查证,明白就行了。但是聊天的时候,一个人哪怕表达了一个不对的观点,但是他用来说明这个观点的知识是非常精彩的,或者说哪怕他这个观点经不起考证,可是他讲段子讲得非常幽默,他能把我们都逗乐,这个也可以学习。
你能欣赏一个人的智慧,而不执着于他的对错吗?有一次我问阿城一个问题:关于《论语》里讲的“吾与点也”。孔子问他几个弟子,你们都有什么志向?最后曾皙说,我就是希望“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窦文涛:聊天的艺术咏而归”。孔子最后认同这个学生,说“吾与点也”。有次闲聊我问阿老:孔子是儒家,可他认同的境界,就是曾皙说在大自然中洗澡吹风唱歌啥的,怎么感觉有点像道家?阿老当下一句让我一点就通,但他的解释我估计学术上许多学者不能同意,但是里头智慧的闪光你能不能欣赏?他说这个“咏而归”,儒道的区别在“归”不“归”:庄子是放浪于天地之间,儒家是放浪完了之后,这个“归”他还是要回家的,回到他的正常人的生活当中,回到社会的秩序中,家庭的秩序中,所以你看儒家讲的是“咏而归”。而道家他感觉自己与天地同化,他不回家了。对《论语》里的“归”字,难道是这么理解吗?我都不太相信。可是你佩服不佩服?一个人你问了他一个问题,他当下就回答了。这里面有他对道家和儒家的认知。妙啊!所以很多人只知道对错,我觉得真是得不到东西。
所以我说对错实在是一个太窄的向度了,人的表达里蕴含了无穷的智慧。你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,你不必执着于对错。如果你的职业需要你辨证真伪,为了你的职业,你可以去做这个事。我也不是这个职业的,我不负责给人纠正对错。如果是在节目里,我要纠正也是因为公共媒体的需要,而且我往往也不会采取反对的态度。我会说,还有这样一种说法,或者我们还查到一个资料,他好像跟你说的不同,就行了,起到一个注解的作用。我觉得如果你非要把人灭了,首先我并不感到满足,我只会感到难过。我希望每个人都畅所欲言。
能承载观点的等量齐观聊天是最好的平台
北青艺评:“聊天文化”如果说得再大一点,哈贝马斯讲过一个“交谈理论”。在尼采宣布“上帝死了”之后,世界开始进入“后真相时代”,韦伯认为“诸神之战”这是现代世界无法解决的问题。后来,哈贝马斯抛出了“交谈理论”,他认为人和人之间通过交谈理性是可以在公共领域达成某种共识的,这后来成了新闻业的黄金守则。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被瓦解了,人类重新进入部落时代。
窦文涛:你讲哈贝马斯,过去我们说起欧洲,总觉得民主就是投票,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有一个前提的。普通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一项政策的背景?你对一个事根本不了解,你投的票有什么意义?哈贝马斯的理论是说,在投票之前要有一个公共讨论的部分。正是通过电视上的脱口秀和访问,才得以让选民知道我们要投的这个议题有几种意见,每一种意见代表人在台上充分地阐述。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当然不可以定是非,这是观众选择的。我们作为主持人应该做到的是让每一个人把他的观点解释清楚,然后再让观众们做判断,做选择。
我们当今很多人可以直接下判断,比如很多自媒体。有人说言论自由,我凭什么不能下判断?可是你对张廷济的说法下判断,恐怕你得先知道张廷济是谁;你对颜真卿的书法下判断,恐怕你得对颜真卿略知一二。就是这样的。很多人是没有一没有二,就对三做评论,你的这个评论值得重视吗?哈贝马斯的理论就是给聊天有了另一种社会意义。的确对社会上很多事情,我们需要有认知。而这个充分的认知、不被人带偏的认知,需要把各种观点等量齐观。什么样的平台能够承载这样的一种观点的等量齐观?我认为聊天是最好的平台。
北青艺评:观点的多样性,跟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重要。
窦文涛:对。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态度太多,了解太少;判断太多,认知太浅。我不大喜欢注意力只放在观点上。我有一个更广的概念,就是语言。我们可以语言审美,我更感兴趣是他如何表达他的观点——这里面有很多智慧、美感。相对于观点我讲语言,相对于情怀我讲状态。我觉得更好玩的是人的状态。不是说人有什么情怀,而是说人在不同状态下他的表达是不同的。
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,我看过很多都忘了,但我就记住一件事,当年古波斯的那些大臣们太逗了。希罗多德记载说波斯人在喝醉的时候做的决定,他们都不能执行。他们要到第二天清醒的时候,大家再复核一遍,然后才付诸实施。这是一个决策过程。这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?反过来也一样,他们在清醒的时候做的决定,他们一定要在喝醉的时候再复核一遍,然后再执行。我觉得这个太逗了,意味着你在两种状态下都觉得好才叫好。
其实决定人的更根本的是你当时处于什么状态,所以状态和语言又是完全不可分的。维特根斯坦老想搞清楚语言确定的意义,他甚至较劲到什么程度呢,比如你说“树”这个词,对应的现实中确实有树,但你说“上帝”这个词,对应的是什么?“所有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保持缄默”。
维特根斯坦还说,语言是不能脱离情境的,语言没有独立意义,脱离情境的语言完全没有办法定义它。这就让我想起了今天的网络上那些指控、八卦等等。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,我们忽略了语境。你知道同样的语言,如果我们不关注他具体说话的状态,就去批评他,那是空的、是虚妄的。一个人躺床上说的话,和在社交场合说的话;一个人在节目里说的话,和他跟老婆说的话,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,你不能根据他说的某一句话就定他的是非,你还必须要问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?他对谁说的?他是在什么场合说的?你只有结合这些才能够正确理解他的这句话。这些道理说白了谁都懂,但是为什么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呢?
出口成章未必最好出口成话才对
北青艺评:因此《圆桌派》显得异常珍贵。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常常因为观点而反目成仇的时代,它示范了一种正常的人际间的交谈是什么样的。说到语言的审美,在某种意义上和小说戏剧的艺术是相通的。
窦文涛:对。一个小说写得好,只是故事好并不是最重要的,比如王朔、金宇澄,其实他们最大的文学上的意义,我认为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。
北青艺评:《锵锵三人行》在当时其实也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。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说,中国电视史上终于有了一档“不装”的节目。
窦文涛:这里面有两个层次:首先,在语言的表层,我们能不能像日常生活里的语气、音调那样说话。今天大部分互联网上的节目都已经是这样了,但是在1998年的时候,即便是这个语言表层的改变都需要灵魂深处闹革命,是很难的。因为我们都是在那样的一个共同历史下长大的,演讲腔、朗诵腔、播音腔、话剧腔……甚至有些文青是文艺腔,这个腔是怎么来的?这个腔是社会和教育建构给我们的。
所谓“说人话”在今天似乎已经不太难了,越来越多的场合里大家说话和生活中没什么两样了,语言的表层似乎是越来越通俗了。
可更重要的问题是深层,这就跟心有关了。也许表面上你的语音语调已经像日常生活里一样了,但更深层的是像一个真的人一样思考,这就更难了。我们说内容大于形式、形式大于内容。其实形式就是内容: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,你的心慢慢会改变,你自然地会趋向于像世俗的人一样思考,像在私人生活里一样去想一个问题,像真实的朋友交际一样去想问题,所以这个诱发了内在的转变。这个转变到今天也没有停止。
因为你的节目是要播出的,不得不有公共话语受限制的部分,可是你要在里面找跟你的私人话语重合的部分。听阿城老师说过一句,你找到了限制就找到了自由。还有一导演调侃我说,“你也说假话,但是你说的时候能让别人知道你在说假话”。到最后我发现实际上就是为了生活里的真实,一切就是为了生活里的真实。当然你把聊天做成了节目,这就像是画,我们叫高仿。我认为最好的聊天,当然不是发生在节目里。
北青艺评:西方人有一个词语,undertable,很形象。最精彩的聊天一定是在桌子底下的。
窦文涛:对,桌子底下的,我到今天还这么认为。但是我们可以有目标,我们可以追慕那个境界,我们能够无限地接近那个桌子底下的谈话状态。我们在公共话语的限制之下,但是你要有这个审美的境界,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的。咱们做高仿,你做到最好的也就是“下真迹一等”——比真的当然有差别,可是你心里至少知道那是美的。
这里面还关乎一种你认为什么样的谈话是美的。比如我们比较容易认同“出口成章”,在我看来出口成章不见得是最高的美。如果一个人他说出的话,我们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文章,这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吗?出口成话才对。文章就是文章,口语就是口语。有些东西是语言的缺点,比如我也在更正自己。我选嘉宾我觉得你可以嘴笨,但是你要有见解,你的见解能服人,你的见解让我们喜欢。这个真理是文从字顺地说出来,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出来,我认为是同样的价值。
北青艺评:结结巴巴里面有一些停顿和留白,会让你去思考。
窦文涛:你说得太妙了,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我说话是有缺点的,我的口才在通常意义上是不好的。那天还有一个观众批评我,我认为他批评是对的。他说我真没法听文涛说话,他说话逻辑混乱,非常跳跃,也不是很干净,嗯嗯哎哎,有的时候有点词不达意。我现在回头看自己以前说话,是比较接近出口成章的,说话很有逻辑性,中间也没什么停顿。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颠三倒四呢?我后来明白了,这像有职业病一样,一个人长期从事一个职业,就改变了他的说话状态。
聊天节目不是访谈节目,聊天主持人有一个特点,他要填满任何一个空白。聊天不像采访,我总是跟嘉宾说,自由地讲,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打断别人,因为生活里的聊天就是这样的。聊天主持人的本能是一冷场了,嘉宾一不说了,我就说。而且我在说的时候,其实我在期待我的话能吸引他插话的兴趣。我希望他能有谈话的兴致。其实我心里在等,希望等到一个点,他说“对”或“不对”,他想插话了,我就随时住嘴让他说,像是自己一边带球一边找人,终于把球传了出去。球场形势瞬息万变,带球找机会的过程也是忽忽悠悠的。所以我说话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到处留空、撒风漏气的状态。我说话的时候脑子里同时有八个想法,而且在判断我要把话题引向哪一个方向他们会有兴趣;我在察言观色,如果发现他好像对我说的这个没有兴趣,马上我就不说了。这个过程每秒钟都在我的脑子里发生。我甚至希望我这个话卖个破绽,因为有漏洞他就可以有兴趣。
北青艺评:难怪你喜欢太湖石,这个形象和你说话的结构很像(笑)。这样是不是抑制了你自己的表达欲?
窦文涛:我的表达欲变得残缺不全,但也很有意思,因为都是一段一段的。也能够满足。光洁如瓷是一种质感,粗粝如陶也是一种质感;完整流利是一种说话的质感,支离拙涩也是一种说话的质感,真的是像太湖石,看的就是漏洞百出又婉转通透,虚实相生又浑然天成。
(北京青年报)